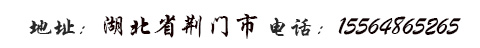那九年连载middot十六
|
刘军连 http://baidianfeng.39.net/a_qwzj/130328/4147810.html 连 载 16 《捉放曹》是戏校打基础的剧目,甭管是什么流派,此戏必学。余叔岩先生在18张半唱片中,就收录过西皮的一段“行路”,二黄的一段“宿店”,足见余先生本人对《捉放曹》的钟爱。 年底,王思及老师给我说了《捉放曹》全剧,曹操由花脸组的田恩荣老师传授。这出戏,和之前学的《文昭关》、《搜孤救孤》、《法场换子》相比,在表演上要求更高些,虽然同属“安工”老生戏,但《捉放曹》故事性强,角色之间的互动更多,就不能只在几段唱腔上下功夫了。戏里有陈宫劝曹操不能妄自行凶的推搡身段,也有陈宫见到毫不知情的吕伯奢时欲言又止的徘徊纠结,以及三番五次阻拦未及而亲眼见到吕伯奢死在曹操剑下的悔恨痛心,直到二人宿店时陈宫想杀曹操而不敢杀的犹豫和恐慌……都对表演提出了全新的要求。而这些表演,都必须通过唱念做表的技术来完成,对于一个刚学了三两出戏的学生来说,着实有点费劲。 我们学戏的步骤,不管文戏武戏,通常是先把零件单独学会、练熟,然后进行组装,最后串起来一遍一遍地走,正式演出前,再进行响排和彩排。日后成了专业演员,因为工作的需要,演出频次增加了,学戏的速度和效率会大大提升,却很难像在科班里学的戏那么瓷实了。学《捉放曹》的过程,也算漫长,尤其花在唱上的时间和功夫。思及老师教戏,表情和肢体语言特别丰富,对我们这种“口传心授”的艺术特别管用,以至于日后每次唱到某一段戏,老师的手势和表情会先浮出记忆来。例如:“一轮明月照窗下”的“下”字,如何做到一口气完成?当时全凭思及老师的手势带领,此处实在无法用文字记录(欲知“一口气”的完成诀窍,请参考喜马拉雅FM《京剧其实很好玩》音频节目第47集)。 学了一整个学期,第一次公演,就在上海兰心剧院。不凑巧的是,在演出的前夜,左眼上长了一个“麦粒肿”,第二天下后台的时候,眼睛已经肿成一个大红包,合不上也睁不开,那一天也是我粉墨登场多年以来第一次想要临阵脱逃。常听老师说,当年某某角儿因为某某事而“回戏”,对此抱有十足的好奇。可是一个戏校小屁孩,能有什么理由“回戏”啊?边学边演,是多好的实践机会,别的同学都巴不能够呢!可是,可是,那时心里就觉着:只有“角儿”才有资格“回戏”,“回”、“戏”,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好帅有没有?那天到了剧场就满后台地跑,见人就给看我的“麦粒肿”,心里打着如意算盘:“看,大家都有目共睹了吧,眼都肿成这样了,还能扮戏吗?万一油彩再感染了可就惨了,再说了,就这样上去演出也影响美观啊”巴拉巴拉……就这样一直等到思及老师到场,顾校长到场,带我医院,挂个五官科,配了一点消炎药膏就把我拎回来,坐在镜子前乖乖地扮戏,开戏了乖乖地上台开唱。与我合演的曹操的扮演者叫高卓,也是当年红极一时的花脸小童星,小小个子,却声如洪钟,唱法相当成熟。多年后改行去了日本,定居在东京,告别了京剧舞台,现在我们只在“K歌”软件里互相PK或者捧场了。 那一次戏终于是没回成,成“角儿”谈何容易。长大后也才明白,越是大角儿,越懂得珍惜每一次的演出,也越懂得该怎样的恪守对人对己的承诺。 《那九年》更多连载,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aizaoa.com/lhgjj/10915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脂肪瘤VS脂肪肉瘤,你还ldquo傻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