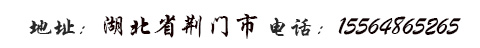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获奖单篇作品
|
《野蜂飞舞》 作者:顾抒 该文获得“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”单篇作品奖,发表于《儿童文学》年第5期增刊。 图片来源网络 “野蜂飞舞,”男孩说,“野蜂飞舞??” “什么?”我不懂他的意思。 “那是一个最好的季节。”男孩说完,又低下头,拿起刻刀继续削着手里的木头。 木头渐渐露出棱角,显出一只动物的形状。 男孩有一双灵巧的手。那是一双修长的、象牙色的手,骨节分明,握着刻刀的时候显得分外坚毅。一下一下地凿在木头上的动作,仿佛一种原始的舞蹈,简直让人着迷。男孩的工作台上摆满了用木头雕刻的动物。他似乎只喜欢刻动物,我没有见他刻过一个人像。 “你坐。” 每一次我到工房来,男孩总是这么招呼一句,手上的刻刀不停。 我就在板凳上坐下来,看他做活。刻刀擦过木头落下碎屑,修光、打磨,用一支硬毛刷着色上光。男孩十岁,是工房的学徒,还在反复地练习。我很喜欢听那“咔——咔——”的单调的声音,有时门外下起雨来,便更觉得安静。 不过,男孩刻的动物只是习作,并不出售,我也不是来买木雕的。 我是来求他修磁带的。 这个年代已经没有人再听磁带了,那是一种已被淘汰的物件。一盘磁带大约巴掌大小,中间有一对“眼睛”,载有磁层的条带就卷在上面,记录着声音信号。把一盘磁带放进机器里,“眼睛”缓缓转动,音乐就神奇般地传了出来。小时候,每个晚上,我都在那磁带转动时富有颗粒感的“沙沙”声中入睡,每个晚上。 但是磁带很容易坏,绞带是最常见的一种。条带一旦脱落,变成乱七八糟海藻似的一团,那就完了,有时候还会断掉—— 我从广播站捡到的那箱旧磁带里,有很多都是这样的。 每天下午放学,我都要去广播站待一会儿。它在树林边的高塔上,大概废弃了许久,一直没有人来。我手脚并用地爬上去,发现窗口筑着麻雀的巢,地上散落着残破的课本、涂了一半的画、一双脏兮兮的球鞋,以及满满一箱旧磁带。唯一幸运的是,广播站的机器还在,插上插头,它就亮起了红色和绿色的灯。把磁带放进机器里,它就唱了起来。 音符拍打着翅膀,从高塔飞向蓝天。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,但那感觉真是好极了,仿佛对一个朋友说出了心里话似的。可惜没过多久,磁带就放完了,剩下的都是坏的。 装磁带的箱子上贴着工房的地址,男孩答应帮我修磁带,但一次只能修一盘。 “多少钱呢?”我问。 “磁带修好了,你听到了什么,告诉我就行。”男孩说,“我每天都在工房里,没有用钱的地方。” 男孩一手托着磁带,一手将铅笔伸进“眼睛”,小心翼翼地转着。于是,那卷成一团的条带一点点展开,回到了应有的轨道上。这修理的方法看起来很简单,我却做不来。至于那些条带断了的,就更加麻烦了,他总是用他那灵巧的手指,变魔术一样将它们捋直、粘连,再卷进磁带里。 “你听过了吗?”男孩问我。 “嗯,只有广播站的机器能放。” “昨天修好的那盘磁带,里面是什么呢?” “哦,是《小狗圆舞曲》。”我说,“一支有名的钢琴曲。” “《小狗圆舞曲》?” “对,据说,灵感来自肖邦的情人乔治·桑喂养的小狗,是一支活泼有趣的曲子。乐曲模拟一条小狗飞快地追着自己的尾巴团团打转,慵懒地躺下来休息,然后又开始游戏,一直到乐曲终了。因为速度奇快,而且在很短的瞬间内结束,所以又叫《瞬间圆舞曲》或《一分钟圆舞曲》。”我连忙从口袋里掏出小本子,抑扬顿挫地读了起来。 本以为这么一来,男孩一定会满意的,不料他却皱起了眉头。 “不,不对。” “怎么了?”我糊涂了,“你不是说,让我听到什么,就告诉你吗?” “你听得不对。” “那??应该是什么呢?” 男孩闭上眼睛,又很快地睁开,认真地看着我。 “我觉得,应该是这样——” 在开满石竹花的原野上, 两只小动物在捉迷藏。 它们玩得那么开心, 戴上一顶草编的帽子,你就找不到我啦。 你就在那里,就在那里,我看见了。 穿上一条树叶的披风,你就找不到我啦。 你就在那里,就在那里,我看见了。 打一个洞,躲进大地的眼睛里,你就找不到我啦。 你就在那里,就在那里,我看见了。 遮住脸,藏到时间的长裙里,你就找不到我啦。 真的找不到你了,真的找不到你了。 一只哭了起来, 另一只掀起长裙的一角, 别哭,别哭,我就在这里,就在这里, 让我送你一朵石竹花。 “别逗了。”我说,“《小狗圆舞曲》就是《小狗圆舞曲》。” 不过,当我回到广播站再次播放那盘磁带时,两只小动物在开满石竹花的原野上捉迷藏的画面总是挥之不去。我关掉音乐,走到窗边,只见高塔下的草地上,有一群孩子在玩耍。 “这一次你听到了什么?”男孩又向我问道。 “你真的想知道吗?”我反问道。 男孩愣了一下。 “可是每一次我告诉你,你都说不对。”我有点恼火,“已经很多次了。” “但真的不对啊。”男孩固执地答道。 我瞪着他看了半天,最终还是屈服了——何必要和一个小孩子较劲呢。再说,他要是生气了,谁来帮我修磁带呀? “好吧,败给你了,这一次是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。” 我忍住心中的烦躁,再一次对男孩解释道。 “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?” “对,据说是德彪西根据诗人李莱的《苏格兰之歌》改编的,先是在年写作了抒情歌曲,后来又创作了同名的前奏曲。” “有歌词吗?”男孩的刻刀停了一下,向我问道。 “就知道你会这么问,我特意抄下来啦。” 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 是谁坐在盛开的苜蓿花丛中, 自清晨起就在放声歌唱? 那是一位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姑娘, 她的樱桃般的嘴唇美妙无双。 在夏日明亮的阳光下, 云雀的歌声在回荡, 爱情在她的心中发芽滋长。 “不对啊,不是这样。”果然,男孩再一次反驳了我。 “你说吧。”我面无表情地说——懒得再和他争辩了。 有一天,一只小动物不小心把她的秘密给丢了,哭了起来。 “你的秘密是白色的还是红色的?”另一只小动物问她。 “我的秘密是蓝色的。”她哭着说,“歌谣一样的蓝色。” “你的秘密是长的还是短的?”另一只又问道。 “我的秘密比一条河还长,比一个字还短。”她还在哭。 “你的秘密是重的还是轻的?” “我的秘密重得像一个夜晚,轻得像天上的云彩。” “那,它有没有手,有没有腿,是不是自己躲了起来?” 这只小动物愣了一下,又“哇”地哭了起来。 “是我把它埋了起来,又忘了地方。” “不要哭,你把它藏在石竹花丛里了,对吗?” 丢了秘密的小动物点点头。 “可是,石竹花丛在哪里呢?” “就在这里。”另一只小动物指了指她。 她低下头,看见自己的心口开着美丽的石竹花,秘密就在那里,它重得像一个夜晚,轻得像天上的云彩,比一条河还长,比一个字还短,蓝得就像一支歌谣,它被深深地藏在那里,埋在石竹花丛里。 说完后,他又低下头,慢条斯理地刻起动物来,就像从没说过这么长一段话似的。 其实,他说得一点道理也没有,但我却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。那盘磁带确实录着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没错,但男孩的语气中包含着某种力量,根本不容我质疑。 “喂,我们俩以前认识吗?”我禁不住问道。 “野蜂飞舞,”男孩说,“野蜂飞舞。” 我不明白男孩在说什么,但他只说了这四个字。 我终于决定,这是最后一次去男孩那里修理磁带。 这盘磁带是巴赫的《哥德堡变奏曲》。 然而,我实在没有心情去向男孩描述磁带的内容。虽然男孩只有十岁,但每一次与他对话都令我感到心悸,仿佛从一条隐秘的小路一直走向一座森林似的。而且,我愈来愈觉得,自己并非是由装磁带的箱子上贴着的工房地址找到男孩的。可是,每当我追问他我们是否原本就认识时,他总是说:“野蜂飞舞。” 男孩稚气的眼神里仿佛含着一种责备,责备我忘了什么不该忘记的东西。 “以后我不会再来了。”我对他说,“箱子里的磁带也修得差不多了,都在广播站放过了。” “这次你听到了什么呢?”男孩就像完全没有听见一样,重复着每一次的问题。 “据说,年到年间,俄国驻德国的德累斯顿大使患上了失眠症,想要听哥德堡弹奏的曲子消磨漫漫长夜,于是委托他找巴赫写一些曲子。因为这位哥德堡不仅是键琴演奏家,也是巴赫的学生。虽然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是假,但确实有许多人喜欢听着《哥德堡变奏曲》入睡。” “你呢,你也喜欢吗?” “我?” “你也会失眠吗?” 我愣了一下,摇了摇头。 “这首曲子确实是关于漫漫长夜的,不过不是你说的那样。”男孩渐渐在木头上刻出两只耳朵。 “我不想再听了。” 从前有一只小动物,它拥有一粒世界上最好的种子。那粒种子可真是好,大大的、圆圆的,就像菩萨胸前挂的佛珠一样。不过,小动物并不知道种子到底有多好,它只是把种子揣在怀里,从原野的这头跑到那头,又从那头跑到这头。 “让我伸出手摸一摸,一会儿它就发芽了。” “不行,它还没准备好呢。” “该拿这粒种子怎么办呢?”小动物问太阳。 “该拿这粒种子怎么办呢?”小动物问风。 “该拿这粒种子怎么办呢?”小动物问雨。 “让我洒几滴眼泪,它一下子就长大了。” “不行,它还没准备好呢。” “让我鼓起嘴吹一口气,吹到哪里算哪里。” “不行,它还没准备好呢。” 小动物想,不如把种子埋进土里,对它说说话吧。 “种子种子,你在做什么?”“我在做梦呢。” “梦见了什么?”“鸟儿在树上歌唱。” “种子种子,你在做什么?”“我在做梦呢。” “梦见了什么?”“池子里的莲花开了。” “种子种子,你在做什么?”“我在做梦呢。” “梦见了什么?”“有一个男孩在向我走来。” 小动物正想对种子说什么,这时,忽然有一只手把种子从它怀里拿走了。从那一刻起,小动物忘了很多事情,忘了它曾为了种子问太阳、问风、问雨,忘了种子曾对它说过鸟儿、莲花、男孩。这不啻是一个漫漫长夜,直到—— “直到什么?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失去了控制。 “直到野蜂飞舞。”男孩说。 “你原本就认识我,对不对?”我瞪着男孩,“快说,是谁派你来找我的?” 男孩看着我,手抖了一下,刻刀划过皮肤,一滴鲜血涌了出来。 “你的手破了!”我连忙捧起他的手。 就在这个瞬间,有一道光从过去而来,照亮了记忆的巢穴,照亮了漫漫长夜,照亮了现在。 “直到野蜂飞舞。”男孩说,而我终于听懂了他的意思。 “是的,野蜂飞舞。”我说。他指的并非一个季节,而是一首曲子——俄罗斯作曲家科萨科夫的弦乐曲《野蜂飞舞》,来自普希金的诗作改编的歌剧第二幕。 男孩抽回手,从工作台下方取出一盘磁带,丢在桌上。 “回去听听吧。” “这个故事里没有石竹花。”我说。 “确实没有。”他说。 我坐在广播站里,机器上的灯明灭闪耀,像一只只昨天的眼睛。 男孩给的磁带就在手边,我把它丢进机器,深吸一口气,按下了“PLAY”键。 《野蜂飞舞》。 机器里漫出音乐的水滴,它们从涓涓小溪变成汹涌的河流,上下翻滚。我捡起课本,抱起画了一半的画,穿上那双脏兮兮的球鞋,走进教室。 “你今天来得真早。”男孩说。 “不是为了排练吗?”我把手里的课本和画丢在桌上。 “对,音乐已经定了。” “快说。” “《野蜂飞舞》。”男孩笑了,“石竹定的,你觉得好吗?” “当然好!” 石竹是我们新来的音乐老师。她才二十多岁,一头长发,就像她的名字一样美丽。以前的音乐老师是一个凶巴巴的老头子,总是骂我们,石竹却有一双梦境般温柔的眼睛,还在她的钢琴上放了一盆花。她弹琴带着大家唱歌时,那花儿也随之摇头晃脑起来。一曲终了,她转过头,眼睛里都是我们的倒影。 这还不算什么,在石竹来以前,我们的音乐课无非是跟着课本哼哼。石竹却有好多好多的点子,小合唱,表演唱,现在又要排演音乐剧了,男生女生无不摩拳擦掌,想要在剧里扮演一个角色。 王子公主另有其人,男孩的角色是王子变成的那只野蜂,而我则被分配去演变成公主之前的那只天鹅,但我们依然兴奋莫名。 “你们要常听不同的音乐。”石竹说,“只听这一首曲子是演不好的。” “下午来我家听音乐吧。”男孩邀请我,“我爸爸还在家里的时候,收藏了好多磁带。” 男孩没有说谎,他爸爸在市里的广播电台工作,不仅有满满一箱的磁带,还有一只高级录音机。只不过,如今男孩的父母已经分开,他就不怎么能见到他爸爸了。 于是,每天放学后,我们几乎都在听音乐。在那沙发前的两只小板凳上,我们听了《小狗圆舞曲》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《哥德堡变奏曲》??啊,那箱磁带简直像个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宝藏! 听音乐的时候,我不和男孩说话,他也不和我说话。我总是在画画,他总是在做手工。男孩有一双灵巧的手,那是一双修长的、象牙色的手,他还有一把孩子用的刻刀。随着乐曲的节奏,一下一下地,木头渐渐在他手中显露出动物的轮廓来。 在路上,我们又说个不停。 男孩告诉我,他自己做的野蜂翅膀被班上演木桶的那个小胖子戳了一个大洞,不得不重新修补。我告诉男孩,家里死活不肯给我买一条表演天鹅用的白纱裙,我只好用纸板画出羽毛的图案作为替代。关于我们听过的每一支曲子,男孩都能说出故事来。他告诉我,《小狗圆舞曲》是一只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玩,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原本是一首诗,失眠的人听了《哥德堡变奏曲》就能安然入睡??他还说,每次一听到《雨滴》就会想到那个下雨天,我们俩坐在小板凳上,用手指在蒙着雾气的玻璃上写字的情景。我们写了自己的名字,还写了石竹老师的名字?? 是的,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石竹老师,她弹琴怎么可以那么优美,唱歌怎么可以那么好听,天下仿佛没有她不知道的事情。如果不是她,我们根本不会开始听音乐,更不可能排演《野蜂飞舞》。 音乐剧的排演已经到了最后阶段,石竹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并不是小孩子的游戏,而是像真正的音乐剧一样,我们出场的时候,她总是走来走去,挥着一只报纸卷成的纸筒说:“不对,不对,你们对音乐的理解不到位!”到男孩家去的时候,我们都不再听其他音乐了,而是反复地听着《野蜂飞舞》。男孩一遍遍地听着那段快如闪电的旋律,磁带到头了就又拿出来再放一遍,天鹅一次次游过我的眼前,但似乎无论如何也不能与自己的角色融为一体。 男孩同时还在用刻刀刻着动物,但即使是我也能看出他并不像往日那么平静。 “你觉得,王子变成野蜂去寻找父亲的时候,是怎样的心情呢?”他忽然问我。 我看着他,一时不知怎么回答。 “如果我也能变成野蜂就好了。”男孩又说。 这时,他握着刻刀的手忽然抖了一下,刻刀划过皮肤,一滴鲜血涌了出来。 “你的手破了!”我连忙捧起他的手。 男孩没说话,就像那只正在流血的手根本不是他的一样。 就在这时,男孩忽然握紧了我的手,几乎把我的骨头都捏碎了,我感到一阵疼痛。但还没来得及出声,他已经很快变得平静下来,我感受到那种平静,仿佛咆哮的大海重新变成一片蔚蓝。 我们就这样握着手,听着《野蜂飞舞》,直到磁带又放到了头,发出了“咝咝”的声响。 “谢谢你。”男孩说。 回家的路上,我始终在想,王子去寻找父亲的时候,是怎样的心情呢?当他变成野蜂越过茫茫大海的时候,是怎样的心情呢?? 不知该怎样帮助男孩,第二天放学后,我悄悄找到石竹老师,把昨天的事情告诉了她。 “你们握手了?”石竹非常惊讶。 “嗯。”我红着脸小声答道。 “你爸妈知道吗?” 我摇摇头,奇怪石竹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,这真的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 而且,她没有给我任何答案,只说了声“你先回去吧”。 又过了几天,我送本子到老师办公室去,推了一下门,门关着,又探头到窗户一看,只见石竹和其他几位老师在一起,正在聊天,就没有立刻进去。这时,我意外地听见了自己的名字,不禁下意识地往窗后一闪,藏起了身影。 是石竹老师的声音。 只听她提到了我和男孩的名字,把我那天悄悄告诉她的事情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,还大声笑着说道:“真是想不到,小男生小女生这个年纪居然会这样,脑子里也不知想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??” “还不是怪你让他们排音乐剧嘛,”另一个老师说,“接触多了,自然会有想法。” 我靠在门边,心中轰然作响,既听不见里面的声音,也看不清走廊外的天空了。一个同学路过,拍了拍我,说:“你怎么了?” “没什么。”我说,然后抱着本子默默离开了。 很快,我就把天鹅羽毛的纸板剪成了碎片,退出了《野蜂飞舞》的排演,而且再没和男孩说过一句话。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aizaoa.com/lhgyf/9240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听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
- 下一篇文章: 回到如果说明天就要分离,让我